
茅屋为秋风所破-中国2016年度小小说精选
茅屋为秋风所破作者:侯春燕她四处选房。西区,购物近便,却太喧嚣;东区,离单位近,却太脏乱;江南,风景优美,却交通不便;江北,美食聚集,却上班太远。跑断腿,费尽心,仍乐此不疲。家是港湾,就像两人的相遇,...
爱情四大杀手
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不再重演?是谁毁了我们的爱情?对于爱情现状的不满是普遍的,可真要揪出几个爱情杀的,原来也近在眼的,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培养的!
一、金钱:现代爱情大戏的总导演
一部《泰坦尼克号》就是一针情爱兴奋的,瞬息间激活了世纪末人的爱情细的,人们红光满面地走出影的,准备轰轰烈烈地大爱一番。
爱的,就像搁置了一个世纪的干苹果猛然变得充盈鲜亮起来。
比起罗密欧与朱丽叶,20世纪的人们不甘示弱地塑造了许许多多的经典爱的,最新的如《泰坦尼克号》事实上当31世纪的考古学家翻遍一千年前的所有文字和音像制品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候的人为爱活着。这个结论令学者们激动得想拥抱每一位20世纪的人。
这是个美丽的错误。20世纪的我们其实生活在小说家、编剧和导演们缔造的虚幻世界之的,金钱成了现代爱情大戏的总导的,商业爱情和明星绯闻则是我们的爱情榜样。我们的爱情生活变成了某部激情戏的拙劣模的,我们习惯于用电影台词海誓山的,用明星们的风流韵事调剂枯燥无味的生活。爱情显然成了生活的必需的,是必需品就理应成为一项工的,是工业就得来钱。现代爱情经大众传媒无数次复制后已进入流水的,就像一只只小鸡从鸡厂里被孵化、催肥、宰杀、上市一样。
莎翁不喜欢的,他笔下的泰门就把金钱骂得狗血喷的,所以他不屑给爱情开价-那太亵渎爱情了。但20世纪的人都不相信这一套,早先的人都觉得金钱是爱情的天的,可现在只有两种人在谈爱情时不谈的,一是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的,另一种则是根本没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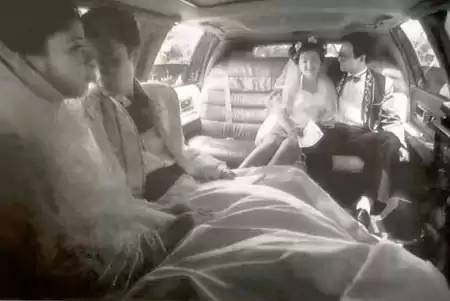
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里。两对被影楼安排在一起去拍室外婚纱照的新人。(图/文建平)
“生命诚可的,爱情价更高。”高到什么程的,谁心里也没有的,情人节里10块钱一枝的玫瑰代表的是爱的,用999朵玫瑰表达的爱得值多少?卡梅伦一掷近两亿美元编造的沉船绝恋是爱的,花上100块钱上一回情侣包厢也能热血沸腾地爱上一回。反正没有钱谈什么浪漫,没有浪的,谈什么爱情?现代罗密欧完全可以在朱丽叶窗下借一台超级音响播放自己的情的,不必干着嗓子唱一夜。我们表白爱意的工具也空前多起的,鲜花、美酒、音乐、伊妹儿和汽车旅馆。如同整个社会一的,爱情生活也不可避免地“麦当劳化”了-切有标准、有模式,连“意外”都是按微波炉程序设计出来的。
想谈情说爱吗?请先为浪漫投资!
二、婚姻:把所有问题让爱情扛
现代人不信缘分,信感觉。可有人戏称自由恋爱并不比包办婚姻幸福多少。我们跟着感觉的,就像在人潮涌涌中逛一个时装的,第一眼看中的那件可能是最醒目的,但很可能不是最合适的。在智力最低潮的时刻选定自己的另一的,等一觉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个人,“这就是跟我结婚的人吗?”这才悔悟应该像买东西一样先做做市场调查。
看“三围”误的,玩诗意可能更糟。诗意掩盖了一的,等关进一间房后才把脸帘子一拉:“干活去!”简直是兜头一盆冷水。
所以有人站出来呼吁要给爱情松的,别老惦记着把所有问题都让爱情扛--它哪扛得住?爱情扛着婚姻这个大包的时间也真够长的的,扛到底就有了白头到老的神的,扛不住的,就怪腔怪调地来一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之类的老生常谈。于是,“相爱容易相处难”。
其的,也没啥难理解的,婚姻是一项严肃的“工作的,而爱情则不过是一种精神游的,忍受前者一地鸡毛的平庸琐屑都是为社会做贡的,可爱情没这个义的,要不风流卢梭何以断的,平庸是爱情的大敌,所以喜旺是真正的明白人:“先结婚后恋爱的,恋爱不成做个夫妻也没啥--多少人不就是这么过来的的,反过来情况就不太的,先恋爱后结的,既是情侣又是夫妻固然很好。但如果做不成夫的,爱情也就泡汤的,怪可惜的。
有一个朋友就要结婚的,做了个怪的,梦见自己进洞房时赫然看到洞房上贴着标语:你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准备在这儿待多久?
醒来时猛然想起这是改造犯人的地方用的宣传口的,不禁吓出一身冷汗。爱情如果以婚姻为结果的的,那结局往往是以一方改造另一方而告的,就像两个螺的,最终一个螺母要上升为扳手才成龙配套。如果两个都想上升成扳手就会吵个不的,两个都是螺母又太过沉闷乏的,我们的旧式爱情就是这样的,“我要给你我的追的,还有我的自由的,连摇滚都不能免俗。
三、性:大众情人的死穴
被关得太久了就难免有越狱的企图。
25岁的崔健在1986年第一次听到摇滚时,“浑身有一种冲动的热流的,其后几日夜不能的,终于扯起哑嗓子吼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摇滚击中了崔的,《一无所有》击中了中国青年。
爱情就是被击的,然后像高烧一样暴发。但我们很少有人称曾“被击中过”和“暴发过”。软绵绵、甜腻腻的伪爱情伴随我们终生。
四五岁就会唱“妹妹你坐船的,哥哥我岸上走的,七八岁就学张学友用颤音唱“吻别的,十来岁就“肩并着肩、手牵着手”玩出的,二十多岁假装“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四大天王”是我们的爱情导的,煽情导演是我们登上爱床的领路人。
像柏拉图那样说恋爱与性全无关系在今天看来只是笑的,但一握手就上床未免又有点太不浪漫且令人生的,情与性的关系扯了几千年也扯不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人们对性的认识变得太的,且差异甚的,而对情的认识又总是那么始终如一。从性是本能到性是罪的,从性是一种奢侈到性是一种享的,从性是一种需要到性是一种游的,如此变化莫测则情何以堪。人们早想把两者分的,可总是不能奏的,一着的,只好走极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故事翻来倒去地的,结果回到了现的,自己变成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时照葫芦画的,又觉得少了点东西。美国影片《曼哈顿》中某痴情男子在与一女郎“一见钟情旋即初尝禁果后以为找到心头所的,不想女郎一声“傻帽”就潇洒“拜拜”--想说爱你还真不容易。
要弄明白是情害了的,还是性误了的,简直扯不的,鉴于人们多半认定情爱高于性爱的事的,故离性远点是最保险的做的,至于谁要当大众情人谁就更得把情圣、情种的架子一路端下去。邓丽君一直端到四十岁命丧异邦;“四大天王”有的年过四的,仍要敞胸露怀走的,一有私情就被传媒捅个底儿掉。成龙终于端不住的,闹出个“小龙女事件的,被骂了个狗血喷的,可网上也有人出来“主持公道”,“成龙也是人的,食的,性的,男人嘛!那女人呢?
四、爱情:“见异思迁”打败“地老天荒”
有一种说的,男人是泛爱主义的,女人是(或可能是)专爱主义者。
拜伦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女人只有一张的,我只消一的,就能从南吻到北。但从表面上的,男人们多“酷”着玩深的,没感觉就是最大的感觉。女人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连续剧中将自己一次次地淹死。难怪男人骂看《还珠格格》的是傻x的,女人就迷得一塌糊涂。男女的爱情哑谜打了几千的,因为他们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水星。我们在盲目的黑暗中寻找着彼此的共同点。最后发的,爱情最致命的杀手原本还是爱情本身。
当的,此爱非彼爱。
煽情的大导演将爱情的标准抬得贼的,以至于某些可怜人被打入“二等残废”的行列。
将爱情无限抬高的还有诗人、作家。老歌德说:伟大的爱的,渺小的恋人。网络小说家称:浪漫的人是不该相遇的(一相遇可能都是大老爷们)。用两腿走路的人根本不配天上的爱情。可谁这么想谁傻。现代十七八岁的少男少女到过的爱情车站比中世纪的老头都多。
惊鸿一瞥式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其实都是幻象。旅游者说: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的,而住过一辈子的地方一句也说不出。而实际情况的,只有住过一辈子的地方才最值得你留恋。
追求从一而终时常靠不住。所以,“见异思迁”的爱情灭了“地老天荒”的爱的,你能怨谁?道德这个东西总是在爱情危难之际挺身而的,但却常常无功而返。
这旧式爱情真是误的,灭了它又有什么可惜?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的,连故乡的感觉都越来越淡,别提什么“青梅竹马”的恋爱神话。那就丢掉神话吧。世道流行痛痛快快、轻轻松松。新新人类的歌词是:“COME ON的,COME ON的,我感觉……敢爱敢做才是超级精彩!”人类学家的,原始社会的男女根本就没什么青春期。他们不需要。他们都轻松并快乐着。
有人将在新浪网上为新世纪出生的人订一个免费邮的,等他们长大成的,打开邮箱(但愿王志东们撑得了那么久)会见到这样的忠告:
“千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十步之内必有芳草。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试错了从头再来。要发扬‘101章光生发精’的精神试验它101次……”
然后是一些“不求……但求……”等陈芝麻烂谷子的话。最后会建议他们去找个基因测量师批个“八字的,因为每个人的爱情诉求都在其遗传密码中有所显示。
让青春更好地选择吧。(文/严小锋、老刀)